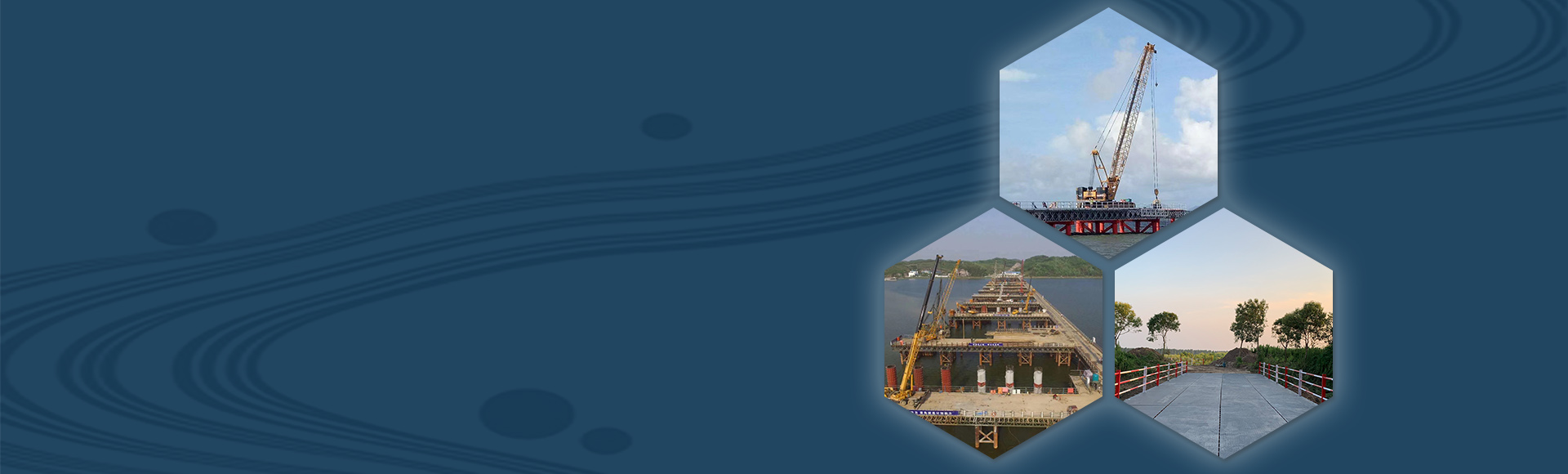一个一般阴天的下午,快5点钟,一名23岁的男人站上了南屏大桥,然后跳了下去。在围观者的凝视下,一位路过的网约车司机,一名路过的外卖骑手,连续一跃而下。

面前是南屏大桥——桥底,垂钓者的聚集地,外卖骑手午休场,中年情侣野餐区。
河水墨绿,被横风吹起细纹,有车通过期,主桥旁的钢便桥会抖,噪音从轮胎碾压的钢板衔接处冒出来——头顶“咯噔”两声,意味着桥上有一台车刚刚驶过。
戴上头盔,鬓角的几缕白头发就盖住了,一米六二的身子蜷进电动车里,掐准时间,把温热的饭盒送到客人手里的时分,有人叫他一声“小哥”。
前山河的水,自西向东穿过大桥,也穿过两岸的白发新城、湾畔雅苑、荣泰城堡、康宏花园,和凯悦嘉轩酒店。
这些地名拗口、生疏,不像邹立彬的茂名老家那些村名来得亲热。但他也现已背熟了,除了地图,乃至对这儿的人感到了了解:这个区域,点外卖的比较多,单价也高一点,小区进出便利,气度的高楼里都有电梯,好送货。这是一个33岁外卖员的自觉。
带着午饭和奶茶,把电动车停在奢华小区门口的时分,他常常会由于再怎样尽力如同也住不进去而有些抑郁。但夜里回到城中村时,看着无数人把骑了一天的车充上电,再把汗湿的短袖泡进盆里,他多少感到些安慰了。
邹立彬持续朝着桥下走,手里拿着头盔,一对兔子耳朵。十年前,在佛山的酱油厂里做维修工的时分,手里拿着的仍是电焊。是,要不是由于参加了那次公司的拍摄活动,要不是就随意那么拍了一下,要不是后来相片被贴在了公司的食堂里,也没有后边什么事了。
坐在酱油厂的食堂里,他第一次感受到愿望的降临。后来他去投靠了一位同学,做拍摄,从助理到自己掌机,从佛山酱油厂到深圳坂田的婚纱店,手里又从电焊换到数码相机,他和十几个人抢一个炽热、拥堵,但修过图后反常梦境的布景里,为客户圆梦,也圆自己的梦。
2012年,邹立彬成为了老公,一年后,他做了父亲。小孩出世的那天,他看着产床上的老婆,听着孩子哭声很透,他眼泪打转,视野含糊。
“那是我人生最感动的瞬间。后来我抛弃了愿望——拍摄。没成婚,愿望是最重要的,结了婚,家人是最重要的,愿望能够放一边。”
“所谓有意义的事都是自己给自己界说的。”他这样跟自己说。他把手里的相机放下,从头进了厂,多赚点钱。疫情三年,他又从厂子出来,戴上头盔送外卖,多赚点钱。

人家都说,曾经送外卖的,一天能拿三四百,现在二百多。但今日跑,明日钱就能到手,人心里结壮。跑外卖也有它的好,自在!邹立彬自诩是个“自在的魂灵”。珠海这座城市,来了四五年,一边送外卖,一边看景色。“周围的人和事,你不看一眼或许就没机会了。”
快5点了。在南屏大桥桥底,邹立彬跟在三个人死后,看他人垂钓。草鱼、鲤鱼、罗非鱼、红眼鱼......白日的单送得差不多了,吃完饭,略微歇一瞬间。
邹立彬的大脑空白了那么几秒,直觉唆使他去找自己的外卖车。他骑上车,往桥中心赶,那里有四五个人现已聚集了。他问人家,有人跳河看到了吗?都说,看到了,但河面那么宽,河水深啊,无法救。
一个瞬间,邹立彬看到了水里的人——如同在动,如同还没有要沉下去的意思,如同自己平常游水那样,头都还在水面上。但漂了一会之后,那人浮起来了,横在水上。
要不要跳?水里的人如同更壮,就这样跳下去了,能不能拖得住那个人?能不能撑到救援的来?救生圈呢?
他又骑上了外卖车。他的眼睛飞速扫过这片高端小区的河道两岸。他要去找救生圈,他要把水里的人救上来。
上午的木匠活完毕得挺早。12点多吃了饭,他顺路到南屏镇看看同村的亲属——在这儿能够讲湖南话。今早跑去帮他人拆门框,老婆于小英总不乐意他干这些,年岁大了,这儿做一天,那里做一天,辛苦不说,钱还不多。曾维龙总觉得,在外面打工几十年了,有朋友叫干活,自己总欠好回绝。
临走前,亲属喊他打会儿牌。他怕堵车,走了。回家得给孩子煮饭。于小英的厂里,今晚肯定要加班了。曾经她在电子厂做线路板,流水线插件。后来厂子一个一个地垮,垮了就得走人,再找下一份工。现在这个做碳纤维杆的厂,上夜班,晚上多少能眯一会。曾维龙也不乐意她干,理由是相同的:一个月两三千块钱,辛苦不说,钱还不多,做保洁都比这个强。
看着时间,4点多走,6点多就能回到中山坦洲的家。今早原本该送小儿子和女儿上学的,谁知道昨夜跟他们俩恶作剧,两人还确实了。
“爸爸每天送你们上学,又要早上,又要烧油。明日车费一人十块,不能记账。”成果今早孩子们爬起来,背着包赶公交去了。这是俩孩子仅有一次没坐自己的车。
等孩子们放学回来,刚好吃口热饭,晚上有空,或许还能再出去跑一会车。跑网约车,于小英也不支持,她说去厂里打听过,他人都说现在没生意,人少车多,自家油车更不合算。但现在日子过得总比俩人刚成婚那会儿强吧?12岁做木匠,做到成婚,乡村的木匠活也只要8块钱一天,肉就要2块钱一斤,得全夹到儿子碗里。

出来打工。夫妻俩跟着湖南老乡,挤在往广东去的大部队里,30多年过去了,总算在中山挤出了一块当地。哪怕仅仅城中村里的两室一厅,哪怕房租一个月也要一千多块,至少三个孩子没留守老家,一家人都在身边。上一年11月,于小英50岁生日那天,他送了老婆一件生日礼物——一串项圈,头一次的。转瞬又要到11月了。
孩子们也大了。大儿子曾晖现已结业,有作业了,能养活自己。操心少了,两个男人的沟通也少了。曾晖给他买过一件短袖衬衫,曾维龙晚上洗了,第二天接着穿,就这样穿了5年。衣服开线了,鞋也掉漆了。
父亲节的时分,曾晖送他新皮鞋、新钱包,现在还在纸盒里放着,曾维龙一次也没有动过。
女儿还小,有时分也会抱怨曾维龙,说自己和弟弟现在在城里读公立学校,不花钱,为什么他还那么累。“现在不要钱,今后读大学也要钱啊,仍是要存一点给你们的。现在精干的动就给你们赚,今后老了去哪里找钱呢?”
再攒点,日子眼看着就好起来了。两个孩子上大学的钱要攒够了,老家盖房子欠的钱也要攒够了。这个国庆,刚回家给老母亲过完80岁大寿。等自己干到60岁,今后就只开车,不做木匠了。人老了。这个事,本年他跟于小英想念了好几回。
10分钟后,下午5点,曾维龙的车通过南屏大桥的钢便桥。桥上有不少人,正在向下看。
随后,他找了桥下斑马线一处停下,人从车里下来,往外跑,跑到了桥上,车门都没有来得及关。
前史仿若重演。16年前,曾维龙的第一个儿子溺亡在湖南老家,家门口那条河里,那条自己学会了游水的河——六年级的儿子摸鱼溺水。
赶回老家的曾维龙,跌进那条河,双手胡乱扑着。水越来越深,直至于小英的腰,她感觉自己要拉不住面前这样的一个男人了,“摸不到的,不要再往前了......”
后来,这个儿子的姓名,成了家里不能提的几个字。偶然被女儿看到了相片,问是谁,曾维龙说自己不认识。仅仅从小水性极好的他,自此再未下过水。

外卖车上的邹立彬着急了。他处处找,哪都找不见救生圈。他决议再次回来南屏大桥。
水里的人,从桥下的一边漂到了另一边,桥上围观的人,就从桥上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。
他在人群中看到了曾维龙。黑色裤子,黑色鞋子,天蓝色的衬衫,看起来人很瘦,表情凝重。曾维龙也看到了邹立彬,穿戴外卖骑手的黄色衣服,气喘吁吁。
“仍是我去救吧。”曾维龙把手机和钱包掏出来,递到邹立彬手里,脱了鞋,往栏杆外翻。
扭头的瞬间,他看到北岸的工地旁,挂着一个明晃晃的圈。“应该是救生圈!我跟大哥说,我说我看到了!工地有一个救生圈,我开车的,我现在就去!大哥说,不用了,来不及了……他跳了下去。”

邹立彬往工地上冲。他扯下救生圈,再次赶回大桥。他看到了,曾维龙现已抓住了水里的生疏人。此时两个人间隔桥面已逾越了30米。
他知道那种感觉。六岁和村里女孩一同学游水,有一个瞬间,女孩如同溺水了,抱着他往河里挣扎。他吓坏了,拼命往岸上游,呛了好几口水。后来所幸无事,这成了他从未提起的隐秘。仅仅那种在水下被人扯住的感觉,他很清楚。
游,拼命游,他边游边喊,大哥挺住,他看到了,他知道曾维龙在硬撑,在等着他,水更急了,邹立彬感觉自己拼命了。
很近了,差不多了,立刻就到了,只要五六米了,邹立彬目测这个间隔,现已满足把救生圈递到曾维龙的手里了。
“就在我眼前,他俩沉下去了。没声音,很爽性,连挣扎都没了。就那五六米啊......人一会儿就没了。”
他往两人消失的方位游,扶住救生圈,用脚往下探,前,后,左,右。前,后,左,右。
安静。什么都碰不到,什么也看不到,水里哪怕一点点黑影都没了,什么都没了......
桥下在产生啥,他不知道,后来他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:曾维龙和跳水者罹难。
再后来,他一向想起那个晚上。“很美妙,也很杂乱。我离我爸出事的当地那么近,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。”
这一个月里,22岁的他,像父亲那样走进了妹妹的家长会,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些中年目光里的惊讶。
他合作派出所的作业,合作来自各方媒体的采访,其他大都时分保持缄默沉静。他告知母亲,别忧虑,会给家里白叟养老送终,把弟妹养大成人。
“我觉得我爸是英豪。这样想,安慰自己。”最近的晚上,一个人躺在家里的木板床上,他总会想起一个画面:那是小时分的乡村,他跟着父亲去奶奶家,路上遇到一棵树。曾维龙告知他,那是枇杷树,然后把他高高举起,放在了肩上。

这一个月里,于小英总是想念,那天在南屏大桥上,一个6岁的孩子跟她讲,跳下水的那个叔叔很英勇。“我说,叔叔英勇?命都没有了啊......”
后来在派出所,她遇见了跳河自杀的男孩爸爸。“我说你儿子自杀,我老公也救人死了,怎样办呢?他说,我只要一个独生子,我的也死了。我说,你的跟我的不相同......我的是救人。”随后两人都缄默沉静了。
这一个月里,邹立彬重复想起那个最终的画面——两人消失在水中的时间。他操控不住自己去假象:假如自己一开始就跳?假如近岸的时分就跳?那后来的工作或许就不会产生。“没有用了,没有假如。”
他不敢见曾晖和于小英,他觉得心里有愧。那天从水里出来,他只给老婆发了微信,没跟爸爸妈妈多讲。后来的工作,是爸爸妈妈自己看到新闻才知道的。母亲大骂了他一顿,父亲笑了笑,没说线号,曾维龙、邹立彬被评为拔刀相助人员。

11月5号,办完了遗体告别仪式,正午于小英给孩子们炖了一锅排骨。后来一家人回了湖南老家办凶事,她发现老家房子的窗户,还有几扇是裂的,家门口的泥地也总得再找人搞一下。半个月后,于小英回到了珠海。那天晚上她下意识觉得,曾维龙总会开车来接她。“周围人家一会儿接电话了,说‘你们到哪里了?’人家都有人接,我没有。没办法。”回到家的那个夜里,她把卫生完全搞了一遍。
邹立彬仍是那个送外卖的,偶然带着单价高一点的温热餐盒,通过这座桥。这儿十分像什么也没产生,除了十几个簇新的救生圈——外包装还没撕洁净,通明的塑料在风里飘。